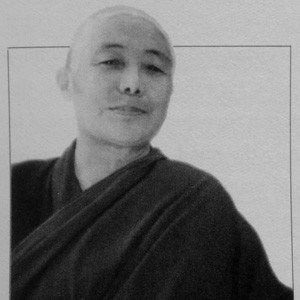恢復古老的傳統
近代中國大陸尼姑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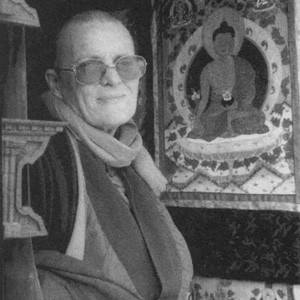
起 佛法之花:以尼姑的身份生活, 1999 年出版。這本書不再印刷,匯集了 1996 年的一些演講 身為尼姑的生活 印度菩提迦耶會議。

比丘尼阿旺曲準
很少有人知道中國大陸尼姑的生活,我有幸親身體驗。 作為比丘尼,我們的其中一位 戒律 是跟隨我們的 烏帕達耶尼- 一位高級比丘尼訓練新比丘尼並充當她的榜樣 - 兩年。 1987 年,當我成為比丘尼時,在我居住的地方,西藏傳統中沒有人能擔任比丘尼的角色。 於是我去了香港,在那裡我遇到了一位我敬佩的來自中國的比丘尼。 雖然我不會說中文,她也不會說英文,但我還是通過翻譯問她,我能不能做她的弟子。 她謙虛地回答說她什麼都沒學到,但我認為這是她謙遜的表現,我對她的敬意也隨之增加。
1994年,我去了她在中國的寺廟 夏日靜修. 後來我和她一起去了地藏聖山九華山,參加了一個大型的出家儀式,她是當時出家的783位比丘尼的總導師。 當我們考慮到共產主義政權在過去四十年中對佛教徒和佛教機構造成的廣泛傷害時,現在中國有這麼多女性想要出家,這是非常了不起和美妙的。
我在中國度過的第一年很艱難,因為我不懂中文。 儘管我努力與尼姑們一起做每一件事,但我還是跟不上。 要學習中文,我會寫一個漢字,然後請人用拼音告訴我,拼音是中文的語音系統。 就這樣,我認識了一些關鍵詞的字,念起來也能跟得上課文了。 不幸的是,天氣太熱,我生病了,不能正常學習中文。
1995 年,我花了 夏日靜修 在我師父在廣州的尼姑庵。 之後,我們在文殊菩薩聖山五台山參加了另一場大型戒律,三百比丘尼和三百比丘參加了戒。 那時我在中國更容易,因為我懂一些中文,而且有趣的是,我並不覺得自己像個外國人。 我穿著中國長袍,和尼姑在一起感覺很舒服。 有時中國的尼姑們想試穿我的藏袍,試穿的時候讓我給她們拍照!
戒律之美
修行初期,尼姑們被教導站如燭,行如風,坐如鐘,睡如弓。 中國人講究的是好看,我的一些行為我覺得還好,結果招來罵。 作為一個外國人,很難分辨什麼好看什麼不好看,尤其是在洗衣服這樣的小動作上。 在我了解我們應該做什麼之前,我在這些文化差異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煩。
有相當多的婦女來到我師父在廣州的尼姑庵要求出家。 他們先由住持面談,如果她認為他們具備必要的資格,就會收留他們。然後他們在尼姑庵做了兩年居士。 這些婦女——大多數是年輕人——留著剪短的長發,在誦經儀式上穿著長長的黑袍。 她們通常在廚房或花園里工作,因為不允許修女們挖地或除草,因為這會傷害昆蟲。
年輕女性進入尼姑庵時,首先被告知的事情之一是,“你必須 亭花,”意思是,“你必須服從。” 這一點很重要,新尼姑們會認真聽從前輩們的教導。 入尼庵至少兩年後,學過沙彌 戒律,並且受過良好訓練,他們可以接受沙彌戒。
之後,當他們準備好時,他們會參加三重戒,那時他們會接受沙彌、比丘尼和 菩薩 誓言. 該計劃包括為期三週的嚴格培訓期。 知道正確行為的最聰明的修女被放在前面並領導其他新手。 每個人都被教導如何穿長袍、走路、吃飯、排隊、鞠躬、使用坐墊——所有這些都是他們在出家和出家期間需要知道的。 他們還學習如何生活 戒律 在日常生活中,每天早上起床、穿衣、系腰帶、上廁所等時,背誦經文。 在那幾周里,來自中國各地和各行各業的各種各樣的人都學習了同樣的基本知識 修道院的 行為。
我師父的庵堂,以書房聞名。 每個人都參加從凌晨 3:30 開始的晨禱 然後我們學習到早餐,根據 戒律 一定要等天亮到可以看到手掌上的紋路後再吃。 我們在餐廳裡穿著正式的長袍,默默地吃飯。 早餐後,我們念經,在尼姑庵做一些必要的工作,然後在佛堂上課。 戒律. 午飯前我們做 供品 到 佛 在主廳,然後魚貫進入餐廳享用當天的主餐。 吃過午飯,大家休息,這個午覺可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下午我們念經,再做一個 供 到 三寶, 然後參加另一個 箴言 班級和小型學習小組。
在平等和尊重的氛圍中,華人修女有強烈的社區意識。 例如,包括住持在內的每個人都得到相同數量的相同食物。 每個人也為公共福祉做某種工作。 一組負責場地和寺廟。 另一個做廚房工作,工作量大而且沒有樂趣,但大家一起工作。 當然,在任何人群中,派別都是存在的,但尼姑們非常慷慨,不佔有自己的一切。
事實上,尼姑們紀律嚴明,不想擁有任何財產。 例如,住持說我可以在房間裡吃飯,因為在炎熱擁擠的食堂裡我很難穿正裝。 寺廟裡最模範的尼姑之一給我帶來了食物。 我想送她一件禮物來感謝她,但即使修女們的房間很少,也沒有她想要的東西。 相反,他們想給予其他人。 例如,當出家時,她們會把衣服拿來送給新修女。 他們喜歡為他人做事,從而營造出一種美妙的社區意識。
比丘尼剃了比丘尼的頭,收那個比丘為弟子,就是對那個比丘尼負責。 她必須保證新尼日後有衣食住行教法。 當我的主人收到特別的 供品 從捐助者那裡,她把它們送給了她的門徒。 當那些東西都沒有了,她所剩無幾時,她把自己的衣服給了他們。 弟子們也對師父負責,對師父十分尊敬。 他們關心她,幫助她完成佛法項目,並按照她的指示修行。
有機會到尼姑庵學習的華人尼姑對此非常感激。 他們盡可能嚴格地遵守法藏部戒,因此紀律很強。 雖然 條件 需要他們處理金錢,這在修女的技術上是被禁止的 戒律,他們背誦一首詩,要求 純化 在拿錢之前。 他們午飯後不吃東西; 如果他們稍後需要服用一些藥物或液體,他們會向另一位比丘尼念誦一首詩,後者以贊同的詩句回應。 他們使用紀律 戒律 在日常生活活動中加強他們的意識。 例如,在進食之前,他們要記住,作為出家人,他們應該配得上供養者供養的食物。 他們記得不要貪吃它,而是把它當作維持生命的藥物。 身體 以修行佛法為目的。
此外,沒有尼姑會單獨外出。 有一次我不得不在尼姑庵外兩步遠的地方清空垃圾,一位尼姑不讓。 當然,由於在西方生活的比丘尼很少,與另一位比丘尼外出並不總是可能的。 當需要旅行時,沒有多少修女能負擔得起兩張機票。 在香港,當我問一個 僧 誰是我們的任命大師之一,他建議我們盡力而為。 找不到比丘尼陪伴,就請沙彌。 若無沙彌,應請居士。 住持說,這些規則主要是為了年輕尼姑的安全而製定的,對於年長的尼姑來說,也許沒有那麼大的危險。
比丘尼必須三修 僧伽: 波薩達, 如果, 和 pravarana。 Posadha 是比丘尼每月兩次的懺悔儀式。 開始前,所有比丘尼剃光頭,然後比丘尼上樓舉行儀式。 很難形容被許多比丘尼包圍,做比丘尼一起做兩千五百年的懺悔儀式是多麼美妙。 佛. 如果有 是在夏季季風期間舉行的為期三個月的降雨撤退,而 pravarana 是結束時的儀式。 在一個我可以和其他修女一起做這些的環境中,參與修女幾個世紀以來認為有價值的傳統,這很鼓舞人心。
實踐與支持
大多數中國尼姑都修淨土法門,念阿彌陀佛 佛,連同一些禪(禪)的做法。 其他尼姑庵強調禪 冥想. 我住的尼姑庵叫路宗,或者 戒律 學校。 在這裡,他們學習和實踐 戒律 在繼續其他實踐之前,至少要詳細了解五年。 我還參觀了一所課程嚴格的比丘尼學院,由五台山一位極其聰明的尼姑開辦。 女性接受兩年的新手訓練; 然後,如果她們做得好,她們就會受戒戒,成為一名預備尼姑。 完成那個訓練後,他們成為比丘尼。 我訪問時大約有一百六十名修女在那裡,學院最多可容納三百名。 他們擠成一排九個女孩,睡在一個大平台上。 他們的長袍和書籍都放在身邊,但除此之外他們一無所有。 他們只是簡單地學習和生活。 這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個藏人 喇嘛堪布晉美彭措仁波切將《龍欽寧提》翻譯成中文,並向數以千計的中國弟子傳授該經文以及其他經典。 許多中國僧人想學習和修行藏傳佛教,但又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們這樣做了。 然而,我認識的修女公開修行。 幾個在做 恩貢德羅是, 初步實踐 西藏傳統,中文。 他們做了 金剛薩埵 百字 口頭禪,一位尼姑已經完成了十萬次大禮拜,而其他尼姑才剛剛開始。
修女們在經濟上得不到很好的支持。 據我所知,政府不支持尼姑庵。 雖然時不時會有施主慷慨地提供午餐,但尼姑們需要從家人那裡收錢才能吃得好。 儘管如此,每個人的食物都是一樣的,而且所有的尼姑都是素食者。 我住在揚州的一個尼姑庵,那裡很窮,因為附近沒有人去過。 政府在公園裡給了這些修女一座破舊的寺廟,讓他們重建。 尼姑們沒有錢,一個老尼姑就坐在外面,對公園裡的路人說:“慷慨布施,功德無量。” 有時人們會嘲笑她,有時他們會給予少量。 漸漸地,修女們艱難地重建了修道院。
廣州最初的尼姑庵建於十七世紀。 文化大革命期間,它被徹底摧毀,部分場地變成了工廠。 之後還給比丘尼,就得等樓裡的在家人搬走。 香港的一些信徒和新加坡的尼姑庵向這些尼姑捐款,現在,十年後,她們的寺廟和尼姑學院幾乎重建了。
政府影響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部分出家僧人都不得不脫俗歸家。 我們的住持被告知要焚燒她的經文和僧袍。 相反,她不顧危險將經藏起來,並割破衣袍,但仍繼續穿著,告訴官員她沒有其他衣服。 多年來她不得不在造紙廠工作,留著長發,但她仍然觀察她 修道院的 戒律. 雙手放在一起時,她用一把扇子遮住雙手,以示尊重 佛. 每當她上香時,她都會在房間周圍灑上香水以隱藏氣味。 仍然有人懷疑,最終她被叫去參加一個政治會議。 顯然,住持與菩薩有著特殊的關係:她向他們祈求幫助,並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個巨人 佛 把一顆巨大的糖果塞進指責她的女人嘴裡。 第二天住持去開會的時候,那個女人竟然沒有開口! 修女們不知何故倖存了下來:她們躲了起來; 他們偽裝自己; 他們試圖融入周圍的環境。 在這些困難的情況下,他們的勇氣、對佛法的信念和堅強的性格令人鼓舞。 但是在安全的那一刻,女修道院院長又剃了光頭。 之後她到廣州四處尋找尼眾,勸說她們剃光頭,重新出家。
儘管中國政府目前表面上給予宗教自由,但仍有許多限制和隱蔽的危險。 政府害怕任何可能有點不同或威脅社會穩定的人。 政府為尼姑庵制定的規則通知貼在牆上。 這些規則通常不明確,因此很難正確遵守。 政府官員隨時可以控告尼姑們破壞她們,給尼姑庵製造麻煩。 政府雖然允許尼姑庵重建,但對出家人數有所限制,出家人還要定期參加政治會議。 我們的住持被召集參加許多耗時的會議,但為了完成任何事情,她必須通過參加這些會議來取悅當局。
成為比丘尼
比丘尼傳承從未在西藏紮根。 西藏婦女很難去印度,印度尼姑很難翻越喜馬拉雅山進入西藏。 不過,似乎有少數比丘尼居住在西藏,並且發現了一些西藏比丘尼出家的記錄。 人們正在研究這個。 許多世紀以前,在朗達瑪國王時期,僧侶的比丘戒幾乎失傳了。 大多數僧侶被殺或被強行脫去僧袍,但三名倖存者逃往西藏東部的康區。 在那裡,他們遇到了兩名中國僧人,他們完成了五名比丘的法定人數才能出家。 如果西藏僧人可以得到中國僧人的幫助,我覺得西藏傳統的尼姑應該能夠得到現在出比丘尼戒的中國僧人和尼姑的幫助。
我覺得成為比丘尼很重要,原因有幾個。 首先,中土在經典中被定義為擁有四類佛教弟子的地方:比丘、比丘尼和男女居士。 如果一個地方沒有比丘尼,那它就不是中土。 第二,為什麼七十歲的尼姑還要出家呢? 當時 佛,女人永遠不是新手; 他們成為比丘尼。 第三,持比丘尼戒以一種非常深刻的方式改變一個人。 這是我和其他成為比丘尼的女性的經驗。 我們覺得對自己的修行、弘揚佛法和利益眾生負有更多責任。 我們的自尊和自信會增加。 因此,我相信如果一個人真的想出家,在某個時候她應該考慮成為比丘尼。
我希望看到比丘尼出家在印度舉行,以便無力前往香港或台灣目前受戒的比丘尼可以參加。 如此,比丘尼 僧伽 會回到它的故鄉。 一些優秀的女修道院院長和 戒律 可以邀請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上師到印度出家。 西藏僧人可以觀禮; 或者如果他們同意,他們可以執行比丘部分的戒律,因為在比丘尼受戒的一天之內 僧伽, 新比丘尼必須由比丘受戒 僧伽.
西方佛教徒可以幫助更大的佛教社區進行跨文化接觸。 因為我們中的許多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從而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文化差異,我們有可能澄清各種佛教傳統之間的誤解。 例如,許多中國人看過密宗圖像,對密宗圖像有誤解 金剛乘. 同樣,許多藏人對其他佛教傳統也有誤解。 重要的是,盡可能多的人與本國和其他國家的其他佛教傳統的人會面和交談。 我們需要保持開放的心態,努力擴大對話,以消除誤解。
尊者阿旺卓卓
比丘尼阿旺曲准出生於倫敦,是一名攝影師。 1977年,她從楚錫仁波切處受沙彌戒,師從頂果欽哲仁波切。 她於 1987 年在香港受比丘尼戒,並在中國大陸師從比丘尼戒律。 她居住在尼泊爾雪謙坦尼達吉林寺,目前正在尼泊爾為藏族尼姑建立尼姑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