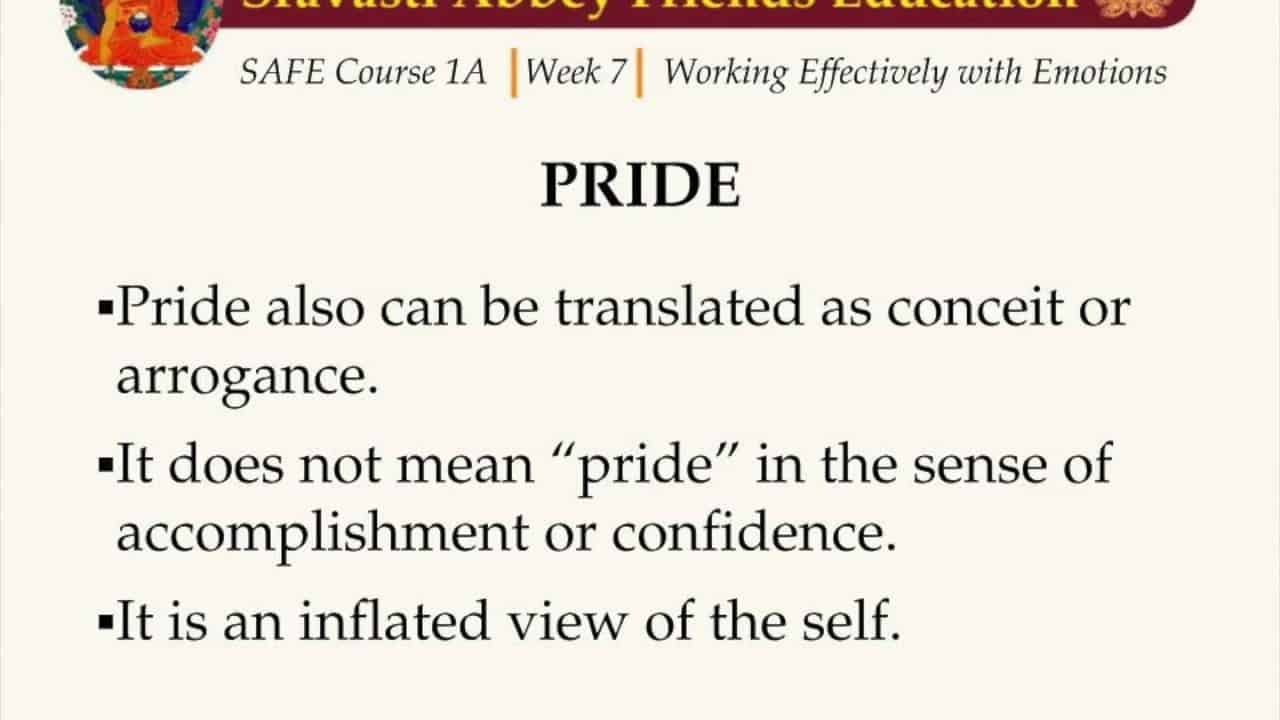睡衣間
作者:JH

我記得宗教為我而死的那一天:那是靈性誕生的那一天。 那時我 12 歲,站在睡衣室裡思考人生。
睡衣室就是我姐姐所說的康復中心紀律室。 它的名字來源於醫院的紙質衣服,還有他們讓你在 The Pajama Room 穿的相配的藍色靴子。
所以我站在睡衣室裡無所事事,只能思考我是多麼討厭生活。 我沒有考慮,因為我特別內省。 The Pajama Room 裡根本沒有別的事可做。 畢竟,睡衣室裡沒有私人物品。 身份在那裡是一種奢侈,很難在白色金屬牆、舖有瓷磚的醫院地板和用作床的體操墊之間找到。
然而,睡衣室有一扇窗戶。 這是圖片窗口大小,非常大。 當然,它是用鋼架和穿過玻璃本身的安全網加固的。 不能讓人們擺脫痛苦,現在我們可以嗎?
看著窗外,就像是在看我生命中的風景。 那是冬天,聖誕節剛過。 窗外有一棵脆弱而沒有生命的小樹。 小草也死了,彷彿在表達對枯樹的愛,與它一起死去。 天空陰沉沉的,彷彿太陽再也不會照耀了。
我花了很多時間看著窗外,想知道我是怎麼進入睡衣室的; 想知道我會從那裡去哪裡; 想知道生活的安全網是否會讓我失去自由。
在那裡,在我沉思和 憤怒, 它發生了。 我應該看到它; 醞釀了很長時間。 但我沒有。 直到事情發生很久之後我才意識到它已經發生了。 無論如何,它發生在那裡。 上帝死在那裡,而我坐在睡衣室裡悔恨不已。 不是上帝,偉大的老父親,天空中的人物上帝,雖然他是方程式的一部分,但上帝是我之外的任何人或任何東西,可以修復我。
坐在睡衣室裡,思考人生,我終於開始接受大家這麼久以來一直在告訴我的事情。 我被打破了。 不僅僅是一個時不時表現“壞”的孩子。 我完全崩潰了。 我一文不值。
我想我在 The Pajama Room 之前很久就考慮過了,只是沒有接受。 直到那一天,我一直認為有人會把我從自己身邊救出來。 我一直希望有一位偉大、仁慈的天使進入我的生活,讓一切變得更好。 然後,我不再相信了。 我不再相信天使和惡魔,神和女神。 我不再相信任何能使我得救的超自然存在。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並不是我不再相信這些東西的存在。 我有相當長的教會化和神秘主義歷史,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一切,這確保我不會輕易放棄信仰。 在我短短 12 年的生命中,我曾向我讀到過的每一種生命發出懇求:“請停止我生命中的痛苦。”
在 The Pajama Room 裡,我終於接受了它,終於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如果存在這樣的存在,它就是不在乎。 上帝不是救世主,無論他或她採取什麼形式。 我現在笑了,回憶起我的行為的諷刺意味,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對上帝的頌詞。
當我離開 The Pajama Room 時,我回到我的房間以保護隱私。 我站在浴室裡,抓著一次性剃須刀,我說服了護理人員我需要剃掉我的三根下巴毛髮,我把刀片從塑料外殼裡撬了出來。 把它放在我放在水槽上的墨水筆旁邊,我脫下襯衫,低頭盯著我光禿禿的胸膛。 沒有想太多為什麼,甚至沒有想這個符號的意義,我拿起剃刀開始在我的胸膛上雕刻——最重要的是——一個大衛的標誌。 傷口不是很深; 畢竟,這是一把一次性剃須刀。 不過,它們足夠深,足以讓我的胸口出現一顆鮮紅的流血星。 我放下刀片,拿起墨水筆。 我當時不知道紋身墨水和一次性鋼筆墨水有區別。 我撬開筆尖,開始在傷口上塗抹墨水。 我希望這顆星留在我的胸前,提醒世界,是的,我已經崩潰了。 我再也不會忘記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 在我 12 歲的頭腦中,這一行為說明了一切。
好吧,我沒有完成我的目標,星星只持續了一個星期左右。 但我相信那顆星星救了我的命。 如果我沒有找到做出那種反抗標記的內在力量,我可能會屈服於壓倒性的悲傷並結束這一切。 畢竟,那時候我想死,我花了很多時間想辦法不痛不癢地死去。 我的標誌,我反對生活苦難的立場,以某種方式讓我繼續前進。
現在回想起來,對我來說更有趣的是那天在我身上誕生的東西。 就像所有的出生一樣,它以鮮血開始,以淚水結束。 不過,我想你可以說我的分娩時間很長,因為我 12 歲時流血,20 歲時流淚。當我 20 歲時,我坐在牢房裡,終於確信我最初開始做的事情相信所有那些年前。 現在,不僅每個人都告訴我我精神崩潰了,而且在我的牢房裡(行政隔離——單獨監禁——出於紀律原因,同樣如此),我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證明他們都是正確的。 我 是 破碎的。 沒有人來修理我,也沒有希望。
那麼,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說宗教在我心中消亡的那一天靈性就誕生了? 宗教是向自己之外的世界尋求幫助的過程。 宗教正在尋找你周圍的世界來修復你。 我在 12 歲那年在 The Pajama Room 放棄了。 我放棄了世界會永遠修復我的想法。 那是宗教對我的死亡。
那時候我覺得我還不能固定下來,所以不能說靈性在我身上完全形成了。 但是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 種下了種子。 第一次念到四諦的那一天,在行政隔離室——睡衣室,也就是我現在的住處——那一天,我明白了我 可以 固定。 我可以修復自己。 那是靈性在我心中誕生的時候。
可以公平地說,這聽起來很自負。 可以這麼說,看到你不了解我,在我心裡不知道我仍然很傷心。 在我的世界裡,在我看來,錯誤的事情多於正確的事情。 我就是那樣做的。 所以不知道這些事情,大聲疾呼似乎是公平的。
事實上,我離固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有一座恥辱之山,時不時地變得高得令人窒息。 以防萬一我忘記了“破碎”,以防萬一我可能開始認為我還好……我只需要環顧四周,看看“我住的地方”,然後我記得我是怎麼來到這裡的。 我永遠無法收回。 它永遠不會消失。
所以,當我說我是唯一可以修復我的人時,這並不是關於我是否適合這項任務的某種宏大想法。 上帝知道,如果這是決定誰最適合這份工作的面試,我會是最後一個僱用我來修理我的人。 不幸的是,正如我所知,沒有其他人會這樣做,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做到。
這帶給我 觀點。 通常情況下,我們作為美國佛教徒不是作為佛教徒而是作為叛教的基督徒/穆斯林/猶太人/等人來佛教的。 我們來到佛教面前說:“哦,對了; 沒有父子聖靈的事。 但我們真正的意思是“我喜歡那個 佛-上帝的伙伴。 我們的意思是,“好吧,我想找其他人來修理,但他們似乎不適合這份工作,所以我要試試這個街區的新人. 也許他能做到。” 作為一個問題重重的人,我可以告訴你,這個新人, 佛,無法比其他人更好地解決您的問題。
所以,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我真的仍然心碎並且 佛 修不了我,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信念? 為什麼我要相信一個我知道不能做我想讓任何人為我做的事情,在這個世界上或其他地方,我為什麼要相信他的話和教義? 為什麼我要相信一個無法修復我,無法讓我完整的存在?
答案很簡單。 世尊沒有說:“過來,讓我來修理你。” 世尊沒有說:“相信我,我會治愈你。” 他甚至沒有說:“向天空祈禱,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世尊所說的是:“道不在天上,道在心中。” 他只是說:“不要出於恭敬而接受我的話……”世尊說:“如來在世間教導。” 他說的,我在這裡轉述的是,“嘿,放下你的屁股,調整自己,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為你做這件事。”
所以,我可能會崩潰。 我可能有很多行李。 我可能會在這個監獄裡度過我的餘生。 我可能有一個裝滿骷髏的大壁櫥,以至於我需要不止一生來對付它們。 但我會做的。 我會帶著燦爛的佛教徒微笑去做,不是因為我特別正直,不是因為我特別純潔,不是因為我特別慷慨,不是因為我特別慈悲。 但因為我是一個好佛教徒。 我是一個好佛教徒,不是因為我是這些東西,而是因為我渴望成為所有這些東西,與 身體,言語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