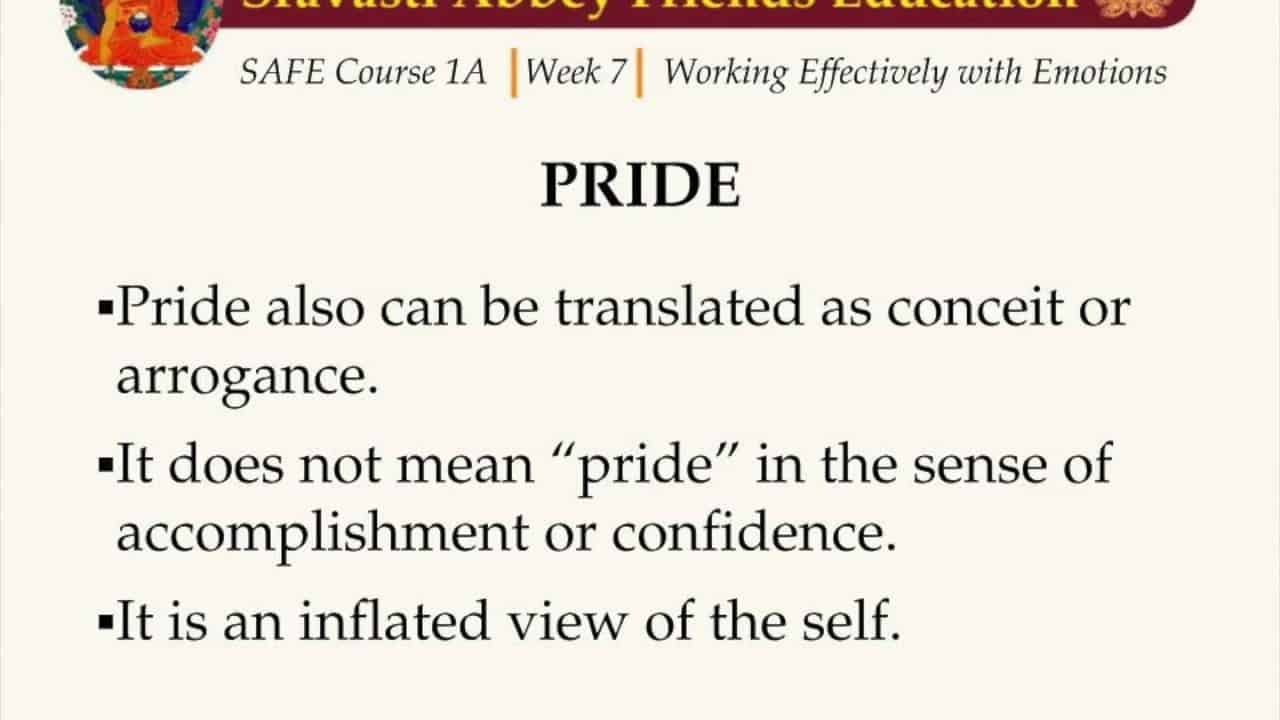睡衣间
作者:JH

我记得宗教为我而死的那一天:那是灵性诞生的那一天。 那时我 12 岁,站在睡衣室里思考人生。
睡衣室就是我姐姐所说的康复中心纪律室。 它的名字来源于医院的纸质衣服,还有他们让你在 The Pajama Room 穿的相配的蓝色靴子。
所以我站在睡衣室里无所事事,只能思考我是多么讨厌生活。 我没有考虑,因为我特别内省。 The Pajama Room 里根本没有别的事可做。 毕竟,睡衣室里没有私人物品。 身份在那里是一种奢侈,很难在白色金属墙、铺有瓷砖的医院地板和用作床的体操垫之间找到。
然而,睡衣室有一扇窗户。 这是图片窗口大小,非常大。 当然,它是用钢架和穿过玻璃本身的安全网加固的。 不能让人们摆脱痛苦,现在我们可以吗?
看着窗外,就像是在看我生命中的风景。 那是冬天,圣诞节刚过。 窗外有一棵脆弱而没有生命的小树。 小草也死了,仿佛在表达对枯树的爱,与它一起死去。 天空阴沉沉的,仿佛太阳再也不会照耀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看着窗外,想知道我是怎么进入睡衣室的; 想知道我会从那里去哪里; 想知道生活的安全网是否会让我失去自由。
在那里,在我沉思和 愤怒, 它发生了。 我应该看到它; 酝酿了很长时间。 但我没有。 直到事情发生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它已经发生了。 无论如何,它发生在那里。 上帝死在那里,而我坐在睡衣室里悔恨不已。 不是上帝,伟大的老父亲,天空中的人物上帝,虽然他是方程式的一部分,但上帝是我之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可以修复我。
坐在睡衣室里,思考人生,我终于开始接受大家这么久以来一直在告诉我的事情。 我被打破了。 不仅仅是一个时不时表现“坏”的孩子。 我完全崩溃了。 我一文不值。
我想我在 The Pajama Room 之前很久就考虑过了,只是没有接受。 直到那一天,我一直认为有人会把我从自己身边救出来。 我一直希望有一位伟大、仁慈的天使进入我的生活,让一切变得更好。 然后,我不再相信了。 我不再相信天使和恶魔,神和女神。 我不再相信任何能使我得救的超自然存在。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并不是我不再相信这些东西的存在。 我有相当长的教会化和神秘主义历史,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这确保我不会轻易放弃信仰。 在我短短 12 年的生命中,我曾向我读到过的每一种生命发出恳求:“请停止我生命中的痛苦。”
在 The Pajama Room 里,我终于接受了它,终于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存在这样的存在,它就是不在乎。 上帝不是救世主,无论他或她采取什么形式。 我现在笑了,回忆起我的行为的讽刺意味,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对上帝的颂词。
当我离开 The Pajama Room 时,我回到我的房间以保护隐私。 我站在浴室里,抓着一次性剃须刀,我说服了护理人员我需要剃掉我的三根下巴毛发,我把刀片从塑料外壳里撬了出来。 把它放在我放在水槽上的墨水笔旁边,我脱下衬衫,低头盯着我光秃秃的胸膛。 没有想太多为什么,甚至没有想这个符号的意义,我拿起剃刀开始在我的胸膛上雕刻——最重要的是——一个大卫的标志。 伤口不是很深; 毕竟,这是一把一次性剃须刀。 不过,它们足够深,足以让我的胸口出现一颗鲜红的流血星。 我放下刀片,拿起墨水笔。 我当时不知道纹身墨水和一次性钢笔墨水有区别。 我撬开笔尖,开始在伤口上涂抹墨水。 我希望这颗星留在我的胸前,提醒世界,是的,我已经崩溃了。 我再也不会忘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在我 12 岁的头脑中,这一行为说明了一切。
好吧,我没有完成我的目标,星星只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 但我相信那颗星星救了我的命。 如果我没有找到做出那种反抗标记的内在力量,我可能会屈服于压倒性的悲伤并结束这一切。 毕竟,那时候我想死,我花了很多时间想办法不痛不痒地死去。 我的标志,我反对生活苦难的立场,以某种方式让我继续前进。
现在回想起来,对我来说更有趣的是那天在我身上诞生的东西。 就像所有的出生一样,它以鲜血开始,以泪水结束。 不过,我想你可以说我的分娩时间很长,因为我 12 岁时流血,20 岁时流泪。当我 20 岁时,我坐在牢房里,终于确信我最初开始做的事情相信所有那些年前。 现在,不仅每个人都告诉我我精神崩溃了,而且在我的牢房里(行政隔离——单独监禁——出于纪律原因,同样如此),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他们都是正确的。 我 是 破碎的。 没有人来修理我,也没有希望。
那么,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宗教在我心中消亡的那一天灵性就诞生了? 宗教是向自己之外的世界寻求帮助的过程。 宗教正在寻找你周围的世界来修复你。 我在 12 岁那年在 The Pajama Room 放弃了。 我放弃了世界会永远修复我的想法。 那是宗教对我的死亡。
那时候我觉得我还不能固定下来,所以不能说灵性在我身上完全形成了。 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种下了种子。 第一次念到四谛的那一天,在行政隔离室——睡衣室,也就是我现在的住处——那一天,我明白了我 可以 固定。 我可以修复自己。 那是灵性在我心中诞生的时候。
可以公平地说,这听起来很自负。 可以这么说,看到你不了解我,在我心里不知道我仍然很伤心。 在我的世界里,在我看来,错误的事情多于正确的事情。 我就是那样做的。 所以不知道这些事情,大声疾呼似乎是公平的。
事实上,我离固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有一座耻辱之山,时不时地变得高得令人窒息。 以防万一我忘记了“破碎”,以防万一我可能开始认为我还好……我只需要环顾四周,看看“我住的地方”,然后我记得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我永远无法收回。 它永远不会消失。
所以,当我说我是唯一可以修复我的人时,这并不是关于我是否适合这项任务的某种宏大想法。 上帝知道,如果这是决定谁最适合这份工作的面试,我会是最后一个雇用我来修理我的人。 不幸的是,正如我所知,没有其他人会这样做,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
这带给我 此 观点。 通常情况下,我们作为美国佛教徒不是作为佛教徒而是作为叛教的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等人来佛教的。 我们来到佛教面前说:“哦,对了; 没有父子圣灵的事。 但我们真正的意思是“我喜欢那个 佛-上帝的伙伴。 我们的意思是,“好吧,我想找其他人来修理,但他们似乎不适合这份工作,所以我要试试这个街区的新人. 也许他能做到。” 作为一个问题重重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新人, 佛,无法比其他人更好地解决您的问题。
所以,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我真的仍然心碎并且 佛 修不了我,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念? 为什么我要相信一个我知道不能做我想让任何人为我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或其他地方,我为什么要相信他的话和教义? 为什么我要相信一个无法修复我,无法让我完整的存在?
答案很简单。 世尊没有说:“过来,让我来修理你。” 世尊没有说:“相信我,我会治愈你。” 他甚至没有说:“向天空祈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世尊所说的是:“道不在天上,道在心中。” 他只是说:“不要出于恭敬而接受我的话……”世尊说:“如来在世间教导。” 他说的,我在这里转述的是,“嘿,放下你的屁股,调整自己,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为你做这件事。”
所以,我可能会崩溃。 我可能有很多行李。 我可能会在这个监狱里度过我的余生。 我可能有一个装满骷髅的大壁橱,以至于我需要不止一生来对付它们。 但我会做的。 我会带着灿烂的佛教徒微笑去做,不是因为我特别正直,不是因为我特别纯洁,不是因为我特别慷慨,不是因为我特别慈悲。 但因为我是一个好佛教徒。 我是一个好佛教徒,不是因为我是这些东西,而是因为我渴望成为所有这些东西,与 身体,言语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