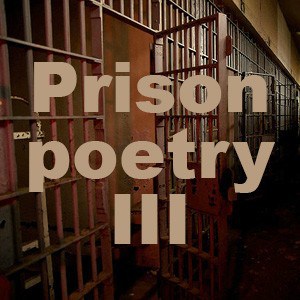前往手术室及其他地方
手术中修持佛法

乔丹是一名针灸师。 在这里,他讲述了他的膝盖手术的故事,以及他如何在整个经历中运用他的佛法修行。 他偏爱在手术期间使用最少的镇静剂反映了他的个人选择,而不是佛教的戒律。
我昨天做了膝盖手术。 在乘公共汽车去医院的前一天晚上,我重读了我的礼貌信,解释了我什么时候不得不停止进食和饮水。 在互联网上做了一些侧面研究并发现这些建议是基于 100 年历史的医学规程之后,我的心绷紧了,发出了一点呻吟,我开始意识到我正在踏上另一段学习之旅,也许每一点都同样具有挑战性作为我穿越中亚前往冈仁波齐峰的独自旅行。
我重新阅读通知,说医院必须依法询问我是否有任何预先医疗指示。 所以我从我的文件中多拿出一份,扔进我的包里,然后拄着拐杖走向公共汽车。
画无常
很快,我就到了术前等候区,脱光衣服,穿上手术衣,凝视着墙上一幅迷人美丽的海景画。 我立刻认出那是我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勾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在背景中,马纳纳岛隐约可见,就像通往未知世界的抽象大门,黑色的圆盘,就像鲸鱼的背部,在缅因州夏日午后波光粼粼的海湾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前景中,一位女士坐在户外木椅上,就在 Monhegan 岛的码头上方,面朝西面,朝向黑暗的门户。
我心想,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提醒我沿途沿着生命海岸的美丽岛屿——无论是字面上的还是隐喻上的。 今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得意地想着。 我等护士回来,慢慢地观察自己的呼吸,又仔细研究了这幅画。 然后我注意到那个女人旁边的三把空椅子。 艺术家是否可以巧妙地将其作为对死亡、朋友离去的提醒? 我越是凝视着西边的微光,即第一人称我们祖先的地方,我就开始漂流到梦想时间——意识到我们过去和未来的生活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当下的生活可以以任何方式结束立即的。 我准备好了吗?
当我 10 岁的时候,我在马纳纳岛遇到了一个隐士。 在我 20 多岁的时候,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偏远的西海岸找到了马纳纳岛的镜像,并在回到西雅图的人行道之前扮演了我自己版本的亨利大卫梭罗几年。 在我 30 多岁的时候,我做了这做那。 到处走走。 我的 40 多岁……快没了。 生命流逝得比流星还快,黎明时的一滴露水,风中的烛火。
在这幅画的边界内,我的眼睛被更深地吸引到神秘、死亡和重生的黑暗岛屿上,随着我的呼吸变得长而深,它继续闪闪发光。 我有些恍惚。 很美味。 然后,我想起了即将进行的手术。 我准备好了吗?
我回忆起我穿越轮回海洋以达到圆满证悟的动机,这样我就可以为其他众生提供最高的服务。 在幻想的土地上停留片刻,平静心灵的水域是可以的,但风暴正在酝酿,船长需要他的智慧,因为汹涌的大海开始堆积在船头上。
清晰地面对恐惧和痛苦
为什么我在这里? 因果报应,我提醒自己。 我自己的迷惑行为导致了这次火车失事 身体 头脑叫做“乔丹”。 我和我认识的其他人一样,不喜欢痛苦。 但我也开始意识到,通过面对痛苦而不是逃避它,一个人可以获得对现实本质的强大洞察力——本性空性,如佛教教义所指的无上智慧心所了解的那样。
我对针灸的小针头很舒服,但更大的针头仍然把我的恐惧计推到红线。 所以这是我的珠穆朗玛峰,我今天的冈仁波齐峰,在刺戳、刺戳和割伤中吸气,让我的意识摆脱对成为这座山的主人的迷惑执着 身体——就好像这是一件永恒的事情。
我要求不要镇静,只要求脊髓麻醉。 外科医生——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他很融洽——告诉我,“没问题。” 但我有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她会把我的愿望传达给她团队中的每个人。 事后看来,我意识到她可能不知道任何一天谁会加入她的团队。
麻醉护士终于回来了,给我量了血压后,她说:“现在我要给你打镇静剂了。” 我想他们已经习惯了大多数人说,“太好了,给我加油。” 尽管我突然感到惊讶,但考虑到我已经明确表示不想接受镇静剂,我还是很警觉地立即说:“我不想接受镇静剂。”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每时每刻保持清醒的心态,就像是掌握了内心平静和精神开悟的钥匙。 这在生活中是真实的,但在临终过程中变得尤为重要。 虽然手术显然是例行公事,但死亡也是例行公事。 总有一天会发生。 除非一个人为那一刻做好准备,否则情绪动荡可能会占上风,而不是自信和冷静的头脑清醒。
对身体的冥想
我的抗生素静脉滴注开始了,我被推进了手术室。 在我生命中被推入手术室(五)的所有时间里,我一直处于全身麻醉状态。 很奇怪,就像做梦一样,被轮子推进去,看到成排的机器和电脑,到处都挂在电线杆上。 我看着护士和医生跳他们的术前仪式舞蹈。 我感到很放松,但也做好了迎接大戳戳的准备,默默地在恐惧之墙上努力。
终于到了这个时刻。 我被要求身体前倾并弓背。 局部麻醉的刺痛并没有那么严重,这是某种东西被强行压入我的脊髓的深度压力。 很奇怪。 但它很快就结束了,我被允许躺下,看着我下体的刺痛 身体 生长。 最后,我的膝盖注射了一针吗啡,我准备好了。
我能感觉到我的膝盖被猛拉到不同的位置,我知道如果没有麻醉,我会感到疼痛,但没有。 然后是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在我膝盖内弹出铆钉,然后是切割工具的声音,刮掉我的半月板软骨。 我开始区分身体感觉本身和我对这种感觉的心理反应。 当头脑收紧时, 身体 收紧。 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个,每次都通过呼吸放松。
焦虑情绪有点高,但我选择了这段经文,即使在那时,我也知道这正是我想去的地方,在我心理舒适区的边缘,从我脆弱的手上凝视着开悟的山顶当下的悬崖峭壁。 我正在学习摆脱强烈的自我——gehechtheid “我”对此有感觉 身体. 这种“学会放手”是任何平静死亡(和生命)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手术是一次为死亡进行彩排并更加专注于生活的机会。
然后就结束了。 幕布落下,我可以看到我的膝盖被纱布包裹着。 外科医生很高兴,并说一旦我从手术中恢复过来,我也会很高兴。 她说,我的膝盖还能再活二十年左右。 我被推到术后恢复室进行进一步观察,在那里我头顶上一位护士说我的静脉系统已关闭并且我非常焦虑。 或许他们忘记了我还算比较警觉,并没有胡思乱想,能够完全听懂他们的谈话。
对美国医疗制度的反思
几个小时后,我的会阴部仍然麻木,我的膀胱里有一升静脉输液。 由于无法自己小便,我在下午 6 点 30 分左右(手术后 XNUMX 小时)被插入导尿管并被扶上了轮椅。 当她推着我走向电梯去见我妻子时,我告诉护士,“我感到非常平静。” 她说,“那是因为你身上有所有的毒品。” 她告诉我,他们确实给我开了抗焦虑药。 当这些东西被塞进我的静脉注射时,我只字未提。
这些药物的管理是否被认为是一种医疗必要性,而不是我本来会有的任何个人偏好? 如果我有选择,我当然会拒绝——宁愿有意识地处理我的焦虑。 我怀疑服用它们是为了加快我的康复速度——放松我的静脉,从而增加我血液中的再氧化过程。 我相信我的 身体 会恢复得很好——在它自己的时间。
我不怕有点着急。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加深我的机会 冥想 实践。 如果人们没有机会拒绝改变思维的药物,而不是让系统不断地推动它们(并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提供),人们还能如何学习用他们的思维工作?
很明显,我希望允许我的 身体 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自行恢复,这与医院工作人员的愿望相冲突,他们希望按时回家,而不必像一位护士所说的那样,四处闲逛等待“讨厌的脊椎病”消退。 与需要较少意识互动的服用兴奋剂的患者打交道可能压力更小。 如果患者的恐惧边缘没有得到测试,那么护士的恐惧边缘被暴露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当然,美国医疗系统中存在不可否认的经济激励措施,可确保药物得到自由分配。 医生、制药公司、医院、企业游说者和国会议员——钱来来去去。
感恩恩情
哦,我可以浪费很多时间咆哮和指责,但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很幸运:我有一个真正关心人的好医生,我给她写了一封感谢信,礼貌地概述了我的经历, 提供 她考虑我的想法。
我能够在不负债(勉强)的情况下支付手术费用,而且我活着讲述了这个故事。 经验教训:总是对我的病人微笑,给予他们我最好的思想和关注。 通过预防性针灸和健康指导帮助他们避免去医院。 当他们需要英雄医院的药物时,通过更多的针灸帮助他们康复。
愿一切众生健康快乐,生于戒德,安详死去,觉悟无上正觉。